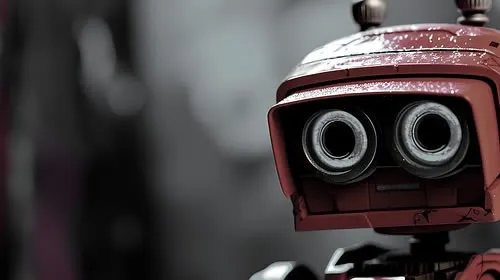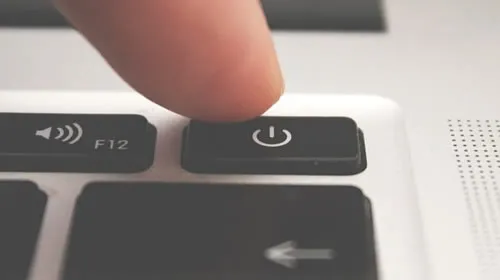分析《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的形象。

《西游记》中最主要的人物不是赴西天取经的唐僧,而是一路上保护唐僧的孙悟空。虽然孙悟空是花果山中一块吸收天地精气的仙石孕育而生的,他的出生充满了神异的色彩,但这个神话人物的性格形象,却有丰厚的生活依据及其现实基础。具体说来,在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大量市井和江湖生活的经验和素材。
悟空最初拜菩提祖师为师,这祖师虽然取的是佛家的名字,却又被人称作神仙,他的言行作为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江湖市井人物。从他身上,孙悟空沾染了一些江湖气息,也开始了解了一些江湖生活的经验,他后来的英雄生涯包括大闹天宫在内,使他变得更加精明敏捷,江湖历练也积累得越来越丰富。
从原型上说,大闹天宫其实只是明清时代小说中市井英雄大闹京都,如《喻世明言》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七侠五义》中的白玉堂闹东京一类故事的翻版。他们的大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往往只是恃才负气,不能容忍别人小觑轻视自己,而极力显露自家的本领,而他们赖以成功的手段,最主要的是神偷善骗的伎俩和随机应变的本事。
孙悟空亦是如此,他的大闹天宫和后来在西天路上降妖伏魔,也主要是以巧偷善骗、灵巧善变这两种本事为凭仗而克敌制胜的。此外,书中的天宫灵霄宝殿、地府森罗宝殿、西天大雄宝殿,也都可以还原为人间的金銮宝殿。孙悟空历尽劫难的西天取经故事的原型,其实是一种闯荡江湖的历险记。
与市井英雄一样,非凡的本领要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考验,好汉的形象也只有经历这种磨练才获得最好的证明。所不同的是,在这里,江湖风波幻化为美丽或狰狞的妖魔鬼怪、险山恶水、毒雾迷瘴、各种诱惑和骗局。至于现实社会的江湖风波中常见的占山为王、拦路打劫、谋财害命,以及英雄们行侠仗义、拔刀相助,在《西游记》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这正成就了孙悟空的出凡入圣的英雄品格。本来,在《大唐西域记》中,西域本身已充满了瑰异的风土景色,经过艺术想象的加工渲染,生成了火焰山、子母河、女儿国等故事单元,更增加了小说的神异色彩。在这种加工渲染中,行旅客商往来江湖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现实依据,使小说中的取经故事内容充实,细节生动。
而市民文学中的英雄传奇传统,也将孙悟空的形象从最初的取经故事中那个单薄的猴行者提升为一个江湖好汉,又从一个单纯的江湖好汉升华为富有使命感的英雄。孙悟空性格形象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取经故事不断丰富、发展,直至在《西游记》中完成、定型的过程。在历史演进中,孙悟空的形象不断丰富充实,并完成了多样性的统一。
在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明之际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唐僧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孙悟空还没有成为整个故事的主角。《西游记》改变了取经故事的传统结构,将孙悟空作为小说的第一号主角隆重推出。小说前七回开门见山,通过对孙悟空神奇的身世和大闹天宫的描写,为英雄人物设计了一个漂亮的登场亮相。
这是孙悟空英雄生涯的开始,接下来除了简短的一段介绍唐僧出场的穿插以外,就展开了西天取经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西天取经当然是全书的主干,而前七回却为后面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作为提供了充足、可信的理由。唐僧的出场被相应地后推至大闹天宫以后,仅这一位置的变更,就足以说明唐僧的重要性在小说中已相应降低了。
实际上,在《西游记》中,唐僧这个人物的作用已几乎淡化成故事的一个缘起,他是支撑取经故事框架的柱子,没有他,取经就失去理由,下面的故事也就无从展开了。在他完成了这一结构作用之后,作者似乎不再保持先前对他的那种浓厚兴趣,将其视同鸡肋,置之不理,因此他的形象相对单薄苍白,缺乏血肉,也不再有发展。
尽管这样,他的软弱、不识世务、慢性子,仍然与坚强、精明、急性子的孙悟空,贪馋动摇的猪八戒乃至忠心耿耿、沉默寡言的沙和尚形成鲜明的对照。唐僧虽然佛学修养深湛,却空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处事能力,其原型来自那些不通世故的书生(书呆子)。小说对他时有温和的讽刺,也可以看作是对明代士人“头巾气”的嘲笑。
观音传授的紧箍咒,在小说中是作为唐僧的权威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使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流于简单化,故事的戏剧性也因之增强了。如果说孙悟空的生活原型来自市井,他见多识广,行走江湖,久经历练,那么猪八戒的生活原型则来自农村,更准确地说,他其实代表的是市井眼中的农民形象。
猪八戒长期住的高老庄,是一个农村式的闭塞环境。他眷恋家园,也正是安土重迁的传统农民意识的反映。个性上,他朴实憨厚,而又常自私地为自己打算;他有一些农民的精明,实际上又目光短浅。他形象粗陋笨拙,可爱亦可笑。他的武器九齿钉钯形状滑稽,让人忍俊不禁。
这钉钯不见于传统兵器谱中,实在是从耕地种菜的农具中衍生想象出来的,却很吻合猪八戒的个性形象。猪八戒在危险关头的动摇、畏缩与孙悟空的坚定、百折不挠恰恰形成了对照。在小说中,他常常是孙悟空耍笑的对象,这正是初入城市的农民常受市民嘲笑的现实的反映。
从这一点上看,《西游记》是站在城市立场上的,它的叙述立场与《金瓶梅》相近,而与《水浒传》的否定城市迥然不同。猪八戒本身的形象特点与市民的审美趣味及其娱乐需要相结合,使猪八戒在小说中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喜剧色彩浓厚的角色。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猪八戒的喜剧使命的实现,有赖于其他人尤其是孙悟空的配合。
孙悟空性格乐观自信,谈吐机智幽默,连妖魔鬼怪也照样戏弄。取经路上,他和猪八戒两人之间插科打诨,调笑戏谑,也为出生入死的漫漫征途增添了不少轻松诙谐的意味。猪八戒这一角色犹如戏曲中的丑角,他的形象塑造显然受了元明以来戏曲传统的影响。同时,《西游记》的语言充满机智、俏皮和幽默,自然是吸收了包括民间说书在内的市井曲艺的语言特色的结果,这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喜剧风格。
一般地说,真正的英雄人物产生于悲剧之中,而孙悟空却是一个喜剧的英雄。这与小说本质上是一部童话有关。童话以儿童的眼光观察世界,洋溢着自由天真的游戏气氛,充满着生动活泼的想象,充满了乐观和希望。童话就是儿童的神话,在儿童的眼里,万物都有生命。
《西游记》是神话题材的小说而富有儿童天真浪漫的意趣,是成功的童话;题材类似的《封神演义》在这方面则失败了,它失在过分虚诞。所谓儿童天真浪漫的意趣,首先指小说多以动物为主角。《西游记》中从孙悟空、猪八戒、龙马到大小山精水怪,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动物,构成了一个儿童们目不暇接的动物园。
其次,对这些动物的观察描写,又处处透出儿童的心理、眼光和兴致,既保留动物的形象特征和生活习性,又融入儿童的心理及性格特征,深受儿童的喜爱。所以,尽管妖魔鬼怪凶恶狰狞,却并不令人恐惧,反而让儿童觉得新奇可喜。猴的顽皮好动,近似儿童。小妖的举止口吻、天真出洋相,也像一群快乐嬉闹的孩童。
第三,孙悟空常视除妖为游戏,声称要顺便抓几个妖精耍耍,而且喜欢恶作剧,这都是儿童典型的生活形态,即生活的戏剧化与游戏化。最后,小说中某些情节的朴拙乃至不合理,甚至前后故事间的非逻辑关系,如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有时不会变化、天篷元帅出身的猪八戒有时竟不会腾云驾雾等,都是合乎童话思维原则,而不宜以成人世界的认真态度对之的,否则便索然无味了。
明代中后期,一批激进的文人致力于追求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如李贽提出“童心说”,提倡童心,即回到人的原初状态,回到心灵天真未凿的状态。《西游记》这一童话能在明代中后期出现,就是以明代中后期追求内心真诚、心灵解放的社会文化思潮为背景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游记》这样一部神话题材的童话小说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